文学的良心——评陈歆耕《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徐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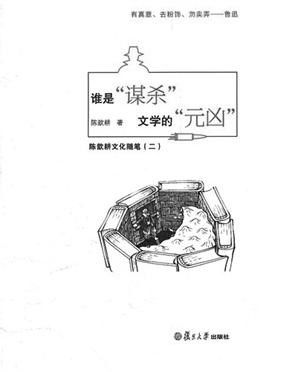 《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陈歆耕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陈歆耕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是近年来颇具分量的一部文学评论集。中国当代文学场域固然是一片繁茂的森林,然而,它所面对的处境,一是历经了十年“文革”对道德的涂炭、对文化的腰斩、对尊严的蹂躏之后,旧的价值体系在崩解,而新的尚未建立;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超速发展,产生了如呼啸列车转弯时的巨大离心力,难免使之在自我重构和外来文化冲击中变形夹生,根基不牢,乱象丛生。此时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对现实的反应能力、发言能力、介入能力、影响能力,全面衰退,日趋疲软,并且双重失语。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多元多义,复杂纷繁,也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讲求“利益大于主义”,呈现了精神的兵荒马乱与文化感的无所适从———中国的文化生态并不因为莫言获得诺奖而莺歌燕舞、满堂皆欢。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之下,作为报告文学家、批评家兼媒体人的陈歆耕,就像是中国文学的一只睿智而勇敢的啄木鸟,以“众醒我醉”的情怀,置利益于身外,对中国文学之殇,勇猛地点穴、触探、批评、建言;同时,又以“众醉我醒”的头脑,保持了高度的理性与清醒,关键是也保持了稳定而明确的价值观念体系与评判坐标。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文化批评之花的根脉供养,源自其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积淀、身为文化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认知能力。《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乃是陈歆耕笔下的中国文学疗伤之日记与实录。
我们注意到,法国艺术大师罗兰·巴特是一个优雅而温和的唯美主义者,他的发言方式完全迥异于他那些战斗的前辈———存在主义者萨特或者加缪,也不同于同代人中的福柯和德里达那样激进的尼采主义者。“他既不想摧毁什么,也不想建构什么”,他只是在愉悦和快感中表达一种对世界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严肃的思想家、伟大的批评家、智慧的哲人。在面对世界之时,他的文字既是他的矛,也是他的盾。我是想说,这样对世界发言的姿态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最妥帖不过的。它既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 既是尖锐的,又是善意的;既是智慧的,又是与世俗烟火相关联的;既是幽默的,又是沉重的……陈歆耕的文学批评即采取了如上的相同方式———他在文字中的迅猛飞翔的姿态让人想起金庸笔下一剑封喉的剑客———四两拨千斤的、点中穴道的,又满怀善意和建设性的。他带着独立的品格和情出由衷的胸怀,目光精准,置喙锐利,由表及里地触碰中国文学的痛点、时代文化的痛点。比如,他说:“心理最脆弱的人往往是人生旅途中最一帆风顺的人,因此稍经风浪即产生恐惧感和崩溃感; 一些作家往往一出道听到的即是一片叫好之声,长期以来也已习惯于被表扬,尽管有些表扬是鼓吹者奉上的 ‘皇帝的新衣’,属于恋爱中鼻子碰鼻子的直吻。一旦被人戳破,其人即做出有异常人的丧失理智的心理反弹。”他说:“为活人尤其是名人写传,具有非常大的难度。要真实地写出传主的人生轨迹、内心世界,不虚美、不掩恶,不仅要经过艰苦采访,还得有极大的勇气。传记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一种,也属基希所说的危险的文学样式。中国缺少敢于冒险又肯下苦功的传记作家。”他的评论准确地刺探到症结的核心处而缓缓给力,往往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他没有犹疑,没有躲闪,没有含混其词。如果说小说家尚可以把自己潜伏于情节和魔幻的背后,批评家则必须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他的观念是藏不住的,他的态度是躲不开的。陈歆耕的批评即是如此。
从《乔布斯传记》到《让子弹飞》,从《古炉》到《生命册》,从“批评家集体失语”到“文学奖乱弹”,从《风语》千万版权到“甘肃八骏”雪漠面对批评时的宽容态度,从张艺谋帝国的衰落到郭敬明的文学幻觉……陈歆耕笔触所及的中国文学场域广阔无垠。他向来强调“新批评”,他的“新批评”可以归结为“三提倡”与“三反对”:即,倡导真诚,反对谩骂;倡导靶向精准,反对言不及物; 倡导活泼幽默,反对枯涩难懂。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聚焦如一盏探照灯,暗的夜连着暗的夜,他却触目惊心地把人们视野中的盲区逐个照亮。
更重要的是,陈歆耕的文学批评呈现了丰富而纯粹的文学性,《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虽然名字刚硬,但逐篇文字却可以被当作散文或者随笔来阅读。这或许与陈歆耕长期写作报告文学相关。阅读该书可以发现,他的批评对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呈现了“散点透视”的样式,却弹无虚发,指向同一个方向。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爱因斯坦对世界最早的感知来源于他四五岁时。父亲给他一个罗盘让他玩,但他惊异地发现,无论他转向什么方向,指针都朝向一个方向。于是他得出结论:在事务的表象背后,一定深藏着一种东西……而后来事实证明,这几乎成为“现实生活”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文化表象”与“文化真相”之间关系的写照。陈歆耕以同样的童稚之心和赤子之心摄取了中国当代文学之势态万象背后的存在,并且将它们深邃地表达出来。当一切喧嚣沉寂下来,他还在默默地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叫做“中国文学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