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让心灵自由飞翔(吴思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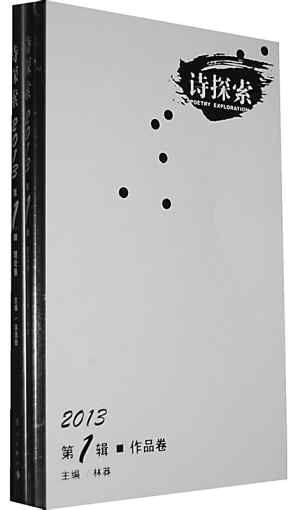
演讲人:吴思敬
简介:
吴思敬先生是著名诗歌评论家,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工作,主要学术著作有:《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冲撞中的精灵》、《诗学沉思录》、《走向哲学的诗》、《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吴思敬论新诗》等。
阅读提示:
■诗永远是心灵的歌唱。伟大的诗人总是有些“想入非非”,他的灵魂是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
■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一个人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的“顶峰体验”,便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此时,审美主体从拘囿自己的现实环境、从“烦恼人生”中解脱出来,与审美对象契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物我两忘、自我与世界交融的状态,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空前的自由感。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
“自由”二字是对新诗品质的准确概括
2005年在广西玉林举行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记者向老诗人蔡其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一下新诗最可贵的品质,您的回答是什么?”蔡老脱口而出了两个字:“自由!”蔡其矫出生于1918年,逝世的时候虚岁是90岁,他的一生恰与新诗相伴,他在晚年所说的“自由”两个字,在我看来,应当说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公布他的日心说的文章(1540年的《初论》)的扉页上曾引用过阿尔齐诺斯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要做一个哲学家,必须有自由的精神。”其实,不只是做一个哲学家,做一个诗人,也一样要有自由的精神。诗歌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心灵活动,常常偏离文化常模,有时还会给世俗的、流行的审美趣味一记耳光,这就要求诗人有广阔的自由的心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诗人的思绪可以尽情地飞翔,而不必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
伟大的诗人无不高度珍视心灵的自由。屠格涅夫在即将退出文坛的时候,曾向青年作家致“临别赠言”:“在艺术、诗歌的事业中比任何地方更需要自由;怪不得连公文套语都称艺术为‘放浪的’艺术、即是自由的艺术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受到束缚,他还能‘抓住’、‘把握’他周围的事物吗?普希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难怪他在那首不朽的十四行诗——每个新进作家都应该把它当作金科玉律,背熟和记牢它——里面说:‘……听凭自由的心灵引导你/走上自由之路……’”
新诗在“五四”时期诞生不是偶然的。郁达夫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由此看来,诗体的解放,正是人的觉醒的思想在文学变革中的一种反映。胡适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谈新诗》),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诗体的变革,这种声音只能出现在“五四”时期,他们谈的是诗,但出发点却是人。
艾青则这样礼赞诗歌的自由的精神:“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宝贵的东西。”(《诗与宣传》)出于对诗的自由本质的理解,艾青选择了自由体诗做为自己写作的主要形式,在他看来,自由体诗是新世界的产物,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此后,废名(冯文炳)还做出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判断:“我的本意,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我觉得,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中“自由诗”的理解,恐不宜狭窄地把“自由诗”理解为一种诗体,而是看成“自由的诗”为妥,废名这里所着眼的不只是某种诗体的建设,他强调的是新诗的自由的精神。
这些诗人在不同条件下关于心灵自由的论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人的心灵是否自由,直接关系到诗人的人格能否健全的发展,诗人想象能否自由地展开,以及最终能否写出富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有了心灵的自由,才可能有健全的、独立的人格。一个伟大的诗人总是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承认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怕世俗的嘲笑和冷眼,无须乎给自己戴一副假面具,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说真话,不去迎合流俗。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坦率地承认:“我并不是一个新人,/这有什么可以隐瞒?/我的一只脚留在过去,/另一只脚力图赶上钢铁时代的发展,/我常常滑倒在地!”郭小川在回顾过去时不回避:“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像这样坦率地自责,这样真诚地自剖,只能出自高度自由的心灵。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绝不会因诗人承认自己的不足而败坏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反,正是在和诗人心灵的撞击中,更感到他人格的崇高。有了自由的心灵,诗人才能超越传统的束缚,摆脱狭隘的经验与陈旧的思维方式的拘囿,让诗的思绪在广阔的时空中流动,才能调动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表象积累,形成奇妙的组合,写出具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诗永远是心灵的歌唱。伟大的诗人总是有些“想入非非”,他的灵魂是可以自由地往返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
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固然,天空是美的,如哥白尼所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空相媲美,能够比无美不臻的天空更美呢!”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天空所能给我们的启发与想象,如同康德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所描写的:“宇宙以它的无比巨大、无限多样、无限美妙照亮了四面八方,使我们惊叹得目瞪口呆。如果说,这样的尽善尽美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那末,当我们考虑到这样的宏伟巨大竟然来源于唯一的具有永恒而完美的秩序的普遍规律时,我们就会从另一方面情不自禁地心旷神怡。”实际上,对天空的关注,更是指把个人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的那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关注。
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诗人郑敏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念书时,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生物学的本能和社会的习俗,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处于混沌的状态。功利境界,是说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他意识到,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立的。人不但须在社会中,始能存在,并且须在社会中,始得完全。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不是以“占有”,而是以“贡献”为目的。天地境界,是指在此境界中的人,知道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在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这样看来,只有立于天地境界的人,才算是“大彻大悟”,才能对宇宙、人生有完全的体认和把握。这样的人,就其形体而言,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就其精神而言,却超越了有限的自我,进入浑然与天地融合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如冯友兰所言:“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三松堂自序》)
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一个人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的“顶峰体验”,便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此时,审美主体从拘囿自己的现实环境、从“烦恼人生”中解脱出来,与审美对象契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物我两忘、自我与世界交融的状态,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
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内心的无限自由对外在的有限自由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从而高扬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
伟大的诗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因为它们传达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成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优秀诗人的身上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梁宗岱在欧洲的时候,一度曾在南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一个五千余尺高的山峰避暑,直到这时,他才体会出歌德《流浪者之夜歌》中最深微最隽永的震荡与回响:
我那时住在一个意大利式的旧堡。堡顶照例有一个四面洞辟的阁,原是空着的,居停因为我常常夜里不辞艰苦地攀上去,便索性辟作我底卧室。于是每至夜深人静,我便灭了烛,自己俨然是脚下的群松与众峰底主人翁似的,在走廊上凭栏独立:或细认头上灿烂的星斗,或谛听谷底的松风,瀑布,与天上流云底合奏。每当冥想出神,风声水声与流云声皆恍如隔世的时候,这雍穆沉着的歌声便带着一缕光明的凄意在我心头起伏回荡了。(《谈诗》)
身兼美学家与诗人双重身份的宗白华也曾描述过类似的心境:
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倜伥,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我和诗》)
梁宗岱与宗白华结合他们切身体验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自我与天地交融的审美心境,这是最好的诗的鉴赏的心境,也是最好的诗的创作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下写出的诗,才能“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梁宗岱:《谈诗》)
创造的成功是自由的实现
当代优秀诗人的作品中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郑敏在西南联大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后,她体会到:“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界限,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点。”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人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刘溜:《“九叶”诗人郑敏》)进入新世纪后,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正是这双有力的手/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最后的诞生……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我并没有消失/从遥远的星河/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
可喜的是,不只是饱经沧桑的老诗人,不少由青春写作起步,而现在已步入成熟的中年诗人,也开始理解并神往这种与自然融合、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蓝蓝说:“宇宙感的获得对于诗人,对于欲知晓人在世界的位置、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直至探求有关认识自我、生与死等问题的一切思想者,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
王小妮说:“让我们回想一下,现在的春夏秋冬一年里面,能有几个朗朗的晴天?如果一个人能在他自己的头顶上,随时造出一块蓝天,只有他才能看见的,是蓝到发紫的蓝天,这不是人间的意外幸福吗。有许多人说,他除了等飞机,三年五年里都没抬头看过天,他活着其实是个负数,是亏损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歌奖获奖演说》)
李琦说:“少年时代,我学过舞蹈。在我眼里,舞蹈老师简直灵异而神奇。她说,把手伸起来!伸向天空的时候,要感觉到手就在长……她还指导我们在舞蹈中发现远方。她说:往远处看,眼里要有一个远方,非常美、非常远的远方……想起遥远的少年时代,我更清楚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越发理解了当年的舞蹈老师。她是那种真正爱艺术的人,犹如我真正需要诗歌。老师的舞蹈和我的写作首先是悦己的,是一种自我痴迷,是心旷神怡。现实生活是一个世界,舞蹈或写作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拥有两个世界的人。现实生活里经历的一切,会在另一重精神世界里神秘地折射出来。实际上,只有在这个虚幻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才能蓬勃而放松,手臂向天空延长,目光朝远处眺望。这才真正是‘诗意地栖居’。”(《李琦近作选·自序》)
蓝蓝、王小妮、李琦均是新世纪以来很有影响的诗人。蓝蓝的话直接表明了她们对天地境界这一人生最高境界的认同与向往。王小妮提出的在自己的头顶上造出一片蓝天,是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了诗人企望一种精神上的提升。李琦从舞蹈老师那里悟出的“现实生活里经历的一切,会在另一重精神世界里神秘地折射出来”,实际也正是由现实世界向天地世界的一种延伸与超越。这些话不同于朦胧诗人的启蒙的宣告,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语言的狂欢,其内涵的深刻与到位,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年轻诗人的成熟。
基于天地境界的诗歌写作即是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
诗人卢卫平从小就有一种对天空的向往,这是母亲留给他的启示:“我四岁时 母亲教我数星星……/母亲说世上没有谁能数完天上的星星/没有谁不数错星星/没有星星会责怪数错它的人/数过星星的孩子不怕黑夜/星星在高处照看着黑夜的孩子/母亲死后留给我的除了悲痛/就是我一直在数的星星。”(《遗产》)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这是由于审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指向抽象的理念世界或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高度肯定和善待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与自由。因此,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俯视大地,重视日常经验写作。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滚铁环,这是诗人王家新儿时与许多孩子共有的人生经验,多年以后他对这一游戏有了新的体悟:
我现在写诗/而我早年的乐趣是滚铁环/一个人,在放学的路上/在金色的夕光中/把铁环从半山坡上使劲往上推/然后看着它摇摇晃晃地滚下来/用手猛地接住/再使劲地往山上推/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如今我已写诗多年/那个男孩仍在滚动他的铁环/他仍在那面山坡上推/他仍在无声地喊/他的后背上已长出了翅膀/而我在写作中停了下来/也许,我在等待——/那只闪闪发亮的铁环从山上/一路跌落到深谷里时/溅起的回音?
我在等待那一声最深的哭喊
如果联想到这首诗的题目是《简单的自传》,那么诗中的滚铁环就不再单纯是一种寻常的游戏,而被赋予了象征内涵。滚铁环的男孩,就像不停地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为了理想永不言弃,这也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写照。在这个滚铁环的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诗人对诗的钟爱,对诗人使命的理解,以及把诗歌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
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俗的红尘遮蔽了人性的诗意本质的时代,不能不让人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命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诗·语言·思》)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立足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创造的成功是自由的实现。让心灵自由飞翔吧,说到底,心灵的自由不仅是创造成功作品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
